目录
快速导航-
星青年 | 影子的影子(组诗)
星青年 | 影子的影子(组诗)
-
星青年 | 时间只是经过(组诗)
星青年 | 时间只是经过(组诗)
-
星青年 | 黑胶摩天轮(组诗)
星青年 | 黑胶摩天轮(组诗)
-
星青年 | 当我们谈论起生活(组诗)
星青年 | 当我们谈论起生活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爱,盛放的意义(组诗)
文本内外 | 爱,盛放的意义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诗歌之于我,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术
文本内外 | 诗歌之于我,理想与现实的平衡术
-
文本内外 | 去龟兹(组诗)
文本内外 | 去龟兹(组诗)
-
文本内外 | 美的补遗
文本内外 | 美的补遗
-
星现实 | 视野之外(组诗)
星现实 | 视野之外(组诗)
-
星现实 | 岁月中转身(组诗)
星现实 | 岁月中转身(组诗)
-
星现实 | 云是水在天上行走(组诗)
星现实 | 云是水在天上行走(组诗)
-
星现实 | 刻心求剑(组诗)
星现实 | 刻心求剑(组诗)
-
星现实 | 幽昧的事物并无二致(组诗)
星现实 | 幽昧的事物并无二致(组诗)
-
星现实 | 柔软之心(组诗)
星现实 | 柔软之心(组诗)
-
星现实 | 旧书市场(组诗)
星现实 | 旧书市场(组诗)
-
星现实 | 孤独的事物(外一首)
星现实 | 孤独的事物(外一首)
-
人间书 | 终南山温故(组诗)
人间书 | 终南山温故(组诗)
-
人间书 | 家有后山梨(组诗)
人间书 | 家有后山梨(组诗)
-
人间书 | 天空下(组诗)
人间书 | 天空下(组诗)
-
人间书 | 你是高悬如云的星辰(三首)
人间书 | 你是高悬如云的星辰(三首)
-
人间书 | 在故乡的屋檐下(组诗)
人间书 | 在故乡的屋檐下(组诗)
-
人间书 | 在字库塔里寻找(外一首)
人间书 | 在字库塔里寻找(外一首)
-
人间书 | 写一些文字抵抗自己的脆弱(二首)
人间书 | 写一些文字抵抗自己的脆弱(二首)
-
人间书 | 沙盘上的帆船(组诗)
人间书 | 沙盘上的帆船(组诗)
-
人间书 | 时光不停挖掘(二首)
人间书 | 时光不停挖掘(二首)
-
人间书 | 愧疚(外一首)
人间书 | 愧疚(外一首)
-
实力派 | 牛儿已不在山坡吃草(二首)
实力派 | 牛儿已不在山坡吃草(二首)
-
实力派 | 孤独的牧羊人(外二首)
实力派 | 孤独的牧羊人(外二首)
-
实力派 | 爱是最短的出路(组诗)
实力派 | 爱是最短的出路(组诗)
-
实力派 | 薄冰(外一首)
实力派 | 薄冰(外一首)
-
实力派 | 存 在(二首)
实力派 | 存 在(二首)
-
实力派 | 川西来信(二首)
实力派 | 川西来信(二首)
-
实力派 | 挖 葛(组诗)
实力派 | 挖 葛(组诗)
-
实力派 | 我的影子爬上矮墙(二首)
实力派 | 我的影子爬上矮墙(二首)
-
山河志 | 风,大地的拾荒者(二首)
山河志 | 风,大地的拾荒者(二首)
-
山河志 | 石 山
山河志 | 石 山
-
山河志 | 时光证据(二首)
山河志 | 时光证据(二首)
-
山河志 | 灵官峡(外一首)
山河志 | 灵官峡(外一首)
-
山河志 | 雪花的多棱镜(组诗)
山河志 | 雪花的多棱镜(组诗)
-
山河志 | 晚 餐(外一首)
山河志 | 晚 餐(外一首)
-
山河志 | 物候盈转低垂(组诗)
山河志 | 物候盈转低垂(组诗)
-
山河志 | 酒与海(二首)
山河志 | 酒与海(二首)
-
压轴 | 在故乡的雪地上(组诗)
压轴 | 在故乡的雪地上(组诗)
-
星干线 | 凹出弧形的中年(外一首)
星干线 | 凹出弧形的中年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桑 树
星干线 | 桑 树
-
星干线 | 老 杉
星干线 | 老 杉
-
星干线 | 花山月酒店
星干线 | 花山月酒店
-
星干线 | 高铁乘务员
星干线 | 高铁乘务员
-
星干线 | 爱的警醒(二首)
星干线 | 爱的警醒(二首)
-
星干线 | 世界地图
星干线 | 世界地图
-
星干线 | 中年境况(外一首)
星干线 | 中年境况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这些年(外一首)
星干线 | 这些年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一百个月夜
星干线 | 一百个月夜
-
星干线 | 比较学
星干线 | 比较学
-
星干线 | 暖冬(外一首)
星干线 | 暖冬(外一首)
-
星干线 | 点 灯
星干线 | 点 灯
-
星干线 | 爱与词
星干线 | 爱与词
-
星干线 | 恰 好(外一首)
星干线 | 恰 好(外一首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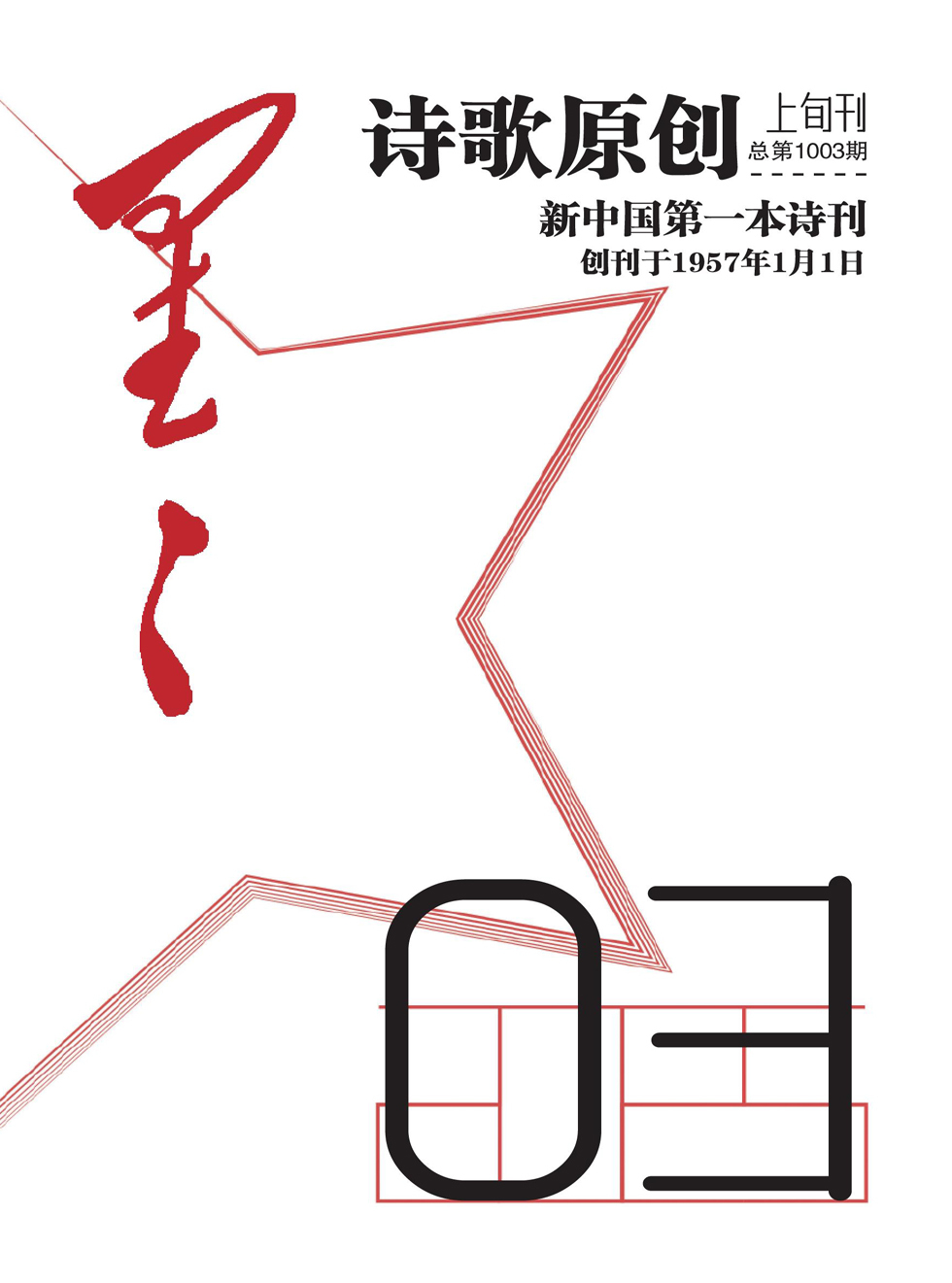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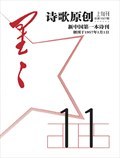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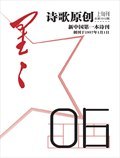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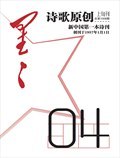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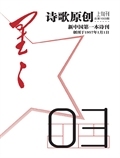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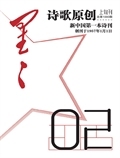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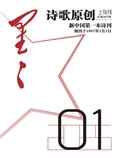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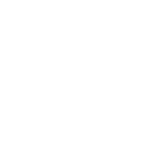
 登录
登录